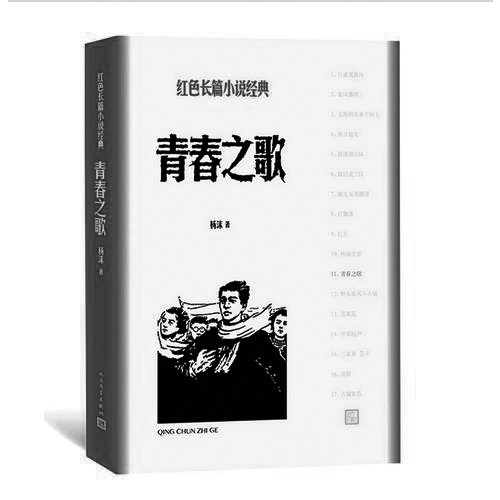


编者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女性求解放求发展的道路走过了一百年,作家们有关女性成长的思考也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本文选取《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为参照,探讨不同时空中女性所面临的自我存在和成长路径问题。作者认为,关于女性的成长,从生命主体和女性存在建构的角度,三部作品做出了不同思考。百年文学史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对话不断开掘深拓,为女性成长和解放开辟出一种新的思考的可能性。
■ 郭力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女性求解放求发展的道路走过了一百年,作家们有关女性成长的思考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在文学史上不断以互文性展开对话探寻,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不同时空中女性所面临的自我存在和成长路径问题。
本文选取当代文学史有关女性成长主题的三部长篇作品《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为参照。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关系到现代女性成长命题,特别是主人公林道静、司漪汶、王琦瑶以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开始起步,时代相同道路选择不同,因主题、因历史语境、因性别因素构成文学史“互文性”对话体系。
《青春之歌》 :女知识分子革命者主体的建立
《青春之歌》在当代文学史上以第一部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写作而著名,文学史对这部作品的意义界定十分明确,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反映时代命题的创作。
作品选取林道静作为主人公,林道静完成的是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最终的转变,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有关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主体完成的历史过程,也完成了《青春之歌》在新中国文学史中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历史地位。
今天从文学创作流变角度可以看到作家杨沫也吸收了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影响,其中林道静历经三次情爱过程,革命与恋爱的关系自始至终都被设置在女性先启蒙后发展的预设框架中,注定林道静是一个被启蒙与成长的典型,所以文本叙事的权威最终显示出女性在革命启蒙话语下必须完成的身份转变。林道静形象是新中国文学序列中党的女儿系列中的一员。
《玫瑰门》 :现代女性精神发展的复杂性
《玫瑰门》是铁凝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序列以母系家族生命史展开。小说中以三代女性的精神发展轨迹来展现历史时代进程中女性的精神发展和裂变。
与《青春之歌》不同的是,铁凝注意到革命话语对于司漪汶来说,始终是一个由于阶级出身问题所不能够完成的内在的焦虑。小说设置了在解放初期司漪汶曾经做过短暂的小学教师和革命干部家庭的保姆,力求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中转变身份,以及她在“文革”中与街道办事处主任罗大妈的“斗法”当中,不断站出来以期获得公开的合法的革命身份。
但小说总是以司漪纹屡战屡败的经历截止或者是中断了人物向革命身份转变的过程。小说以司漪纹内心的强大和精神的韧性对抗来自父权和男权的侮辱与损害,但她始终不能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得自我认知的圆满性。
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司漪纹因身份问题引发内在焦虑意在说明她的不圆满,女性精神解放的求证旨归在压抑中变成了自我指认的焦虑,所以司漪纹作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只能存在于历史的选择中,是一种悬搁状态,也许未完成恰恰是以象征的方式标示出现代女性精神发展和解放探寻的复杂性。
《长恨歌》 :家国大事与小女儿情态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主人公王琦瑶一生不仅是历史时空女性形象的思考观照,而且是有关上海的历史变迁和新时代发展的见证人。王琦瑶以自己生命不变的节拍构成参照系观照大历史的演进,作家坦言“写王琦瑶就是写上海”。
只不过王安忆这一次在思考女性解放和现代意识主体的时候,把人物设置在一个反向成长的路径上。作家避开了有关女性成长的启蒙话语,而以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小的切口从社会生活的最细微处来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变迁。但是善于叙事策略的王安忆,把家国大事与小女儿情态结合起来,在文本中王琦瑶是以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体认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
作家是从生命个体伦理的角度试图通过王琦瑶一生的存在方式反观女性成长的命题。作品中王琦瑶与多个男人的情爱方式看似个人行为选择,实际上后面都有着大时代多种因素的交汇影响,意识形态与个体遥相呼应无所不在,所以不论是在里弄、影楼、片场、爱丽丝公寓、乌桥、平安里,无数个上海空间的位移最后都不能安置王琦瑶的身心,这是一个从未开始成长的上海的女儿。但是王琦瑶的人生脚步却穿越了上海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时空,她的存在是一座城市的存在与记忆。
大历史与女性个体存在
有意味的是上述三部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分别在她们青春起步阶段大致历史时间段相同,但她们的命运在作家的处理之下有了不同的分水岭和人生方向,背后原因是两代作家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不同理解。
《青春之歌》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的主题要解决和完成知识分子最终道路选择的宏大叙事。也因此女性命运与知识分子道路在小说的叙述当中被不断置换成为一个隐喻系统,林道静作为历史镜像成为文本重要的叙事策略。林道静成长为党的女儿,作家杨沫圆满完成了小说的创作宗旨。
而《玫瑰门》《长恨歌》两部作品构思于20世纪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样貌和家族叙事成为当代创作名篇。关于女性的成长,从生命主体和女性存在建构的这个角度作家有了不同的思考,在历史的宏大性与庸常性之间作家开始有了新的选择。
《青春之歌》着眼于时代洪流中的大历史,而《长恨歌》《玫瑰门》却把目光落在历史洪流当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上,也由此作家运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杨沫塑造林道静形象用的是典型化的创作手法,也因此林道静这一典型形象注定代表着一群人难免类型化。而铁凝和王安忆把目光放在大历史当中个体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上,作家着眼的是关于个体空间世俗性、日常性、审美性层面的思考,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作家创作历史观的改变连带着作家创作叙事策略的改变,女性的成长和女性的解放的确关乎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解放。
百年文学史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对话不断开掘深拓,构成文学史不同阶段同一主题不断呼应的互文性书写,达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对话体系。它在对历史的补充判断和反思的过程当中,以文学书写的方式,为女性成长和解放开辟出一种新的思考的可能性。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