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
近期面世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基于田野调查,探讨了迁移背景下,男农民工在恋爱、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养老职责中所采取的权宜性策略,为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性别权力的变动机制、男性气质及性别权力变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该书弥补了男农民工的声音和主体经验在学术探讨中的缺失,让读者看到了性别关系变化的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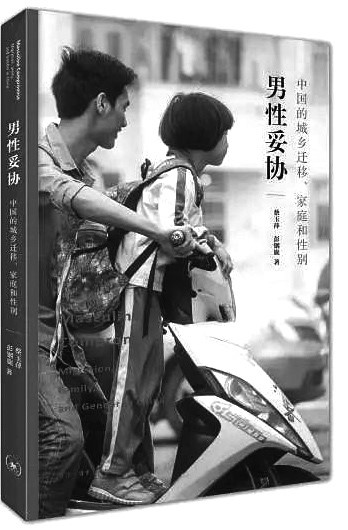
■ 刘天红
近期面世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蔡玉萍 彭铟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版),基于在东莞、广州、深圳三地对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男农民工所做的田野调查,探讨了男农民工在恋爱、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养老职责中所采取的权宜性策略,呈现了男农民工与传统男性气质发生偏离,并与之协商的过程,为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性别权力的变动机制、男性气质及性别权力变化提供了独特视角。
变迁的男性气质
毫无疑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性别秩序在逐渐发生松动与变化。事实上,女性地位崛起早已被视作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性别观念、性别态度变化的研究与讨论甚多,性别观念变化也常常被信手拈来,用以解释其他很多社会现象,比如“她消费”的兴起、低生育率的出现、初婚年龄的延迟等。但关于性别观念如何变化的微观讨论却未必细微明了,相关讨论大多集中在对女性权利、地位、价值观及其对男性权力的反抗上,对站在性别关系另一端的男性着力相对较少。加之,正处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性别关系总是与其他社会因素相互缠绕,考察性别权力的变化并非易事。
《男性妥协》一书弥补了男农民工的声音和主体经验在学术探讨中的缺失,将男性,特别是男农民工纳入讨论,分析了男性气质变化的内在机制,让读者看到了性别关系变化的另一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对男农民工的情感世界做了大量考察,包括其对“浪漫爱情”的欲望,及因处于现代价值与传统义务之间面对求而不得的感情与婚姻时的挣扎;拥有“可敬的男子气概”的男农民工对家庭的供养和关爱;作为外出务工的父亲,面对留守故乡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无力、愧疚、期望、骄傲与失落;作为在外谋生者,面对难以尽孝的困境时,所表现出的不安……在传统男性气质限制下,“情感”对男性而言往往是难以言说的。作者所探讨的男性农民工所面对的迁移的情感后果,是男性气质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为我们打开了探究男性隐秘的情感世界的一扇窗。
基于田野调查的证据,作者为读者呈现了城乡迁移背景下,男农民工基于“生计”的考量,在家庭内部所做出的与传统男性气质的一系列妥协:给予女性管理家庭的权力;基于男性难以一人养家的现实,在“做家务”上做出退让;由于聚少离多,在养育子女方面,渐渐调适“严父”的威权角色,增加了情感沟通的维度;与父母的两地分离,使得男性“孝子”的角色得以重新定义,尽孝的方式也有所改变。尽管作者认为,男性气质的这些改变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但看到男权社会中享受“既得利益”的一方在性别关系上所做出的调整,也总让人对性别关系的变化充满希望。
迁移:改变家庭生活的关键性事件
与此前关于迁移、家庭和性别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同,作者基于实证调查的证据也认为:迁移是能够改变家庭生活的关键性事件,且这些改变都是性别化的。
“迁移”作为一个关键性事件,对农民工家庭生活而言是一个外部诱发因素。农民工往往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而选择向城市迁移,与传统关于迁移者多是未婚工人,即多是打工妹和打工仔的印象不同,男农民工中已婚男性多于未婚男性,且女农民工的数量在过去30年中迅速增长,夫妻双方共同迁移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对迁入城市的已婚女性而言,“迁移”不仅使她们获得了获取收入进而在家庭内与男性协商的机会,最重要还有迁移使其在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与价值规范中“脱嵌”,使其获得更多习得现代价值与观念的机会,而这些价值和观念与传统的性别观念相矛盾。
对男农民工而言,迁移往往使其面临丧失“家庭经济提供者”身份的风险,这也构成了其做出上述种种“妥协”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男性也面临来自城市男性气质的冲击与挤压。相比于城市高收入男性,男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使其面临着一层失落。都市话语所建构出的支配性男性气概,比如“富有的、成功的、人脉很广的企业家”“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精熟、举止得体的专业人才”形象,对不能达到上述标准的男性农民工形成了挤压。此外,都市消费文化,比如与浪漫爱情紧密相连的“都市约会文化”(看电影、喝咖啡、购物、送礼物)也对男农民工的恋爱自主性形成了压迫。迁移进入城市的男性,实则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其男性气概做出调整,并对其所做出的一系列让步做出合理化的解释,进而建构出新的男性气质。
此外,值得关注的则是伴随迁移家庭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所带来的性别观念的徘徊。农民工家庭因为生计而迁移,男农民工因为生计而对男性气质做出调整,但这种调整似乎依然服务于男权社会的重要职能——延续宗族血脉,那些在成婚后依然持续夫妻双方共同迁移的家庭,大多是为了给儿子盖房子、买房子、成家。以此来看,迁移家庭所做出的种种协商、调整,也可视作为了达成延续宗族血脉的目的所采取的暂时性的策略。
关于这种权宜性的男性气质妥协,会伴随迫使男农民工做出妥协的条件消失而复苏,还是会逐渐累积而成为一种新的“惯习”,作者则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这有待于对男农民工及其家庭实践的进一步观察与研究,相关结果将丰富对现代性别观念的探讨,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征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