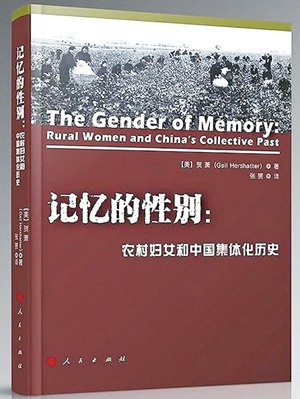
阅读提示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搜集了72位陕西农村60~80多岁老年妇女关于20世纪中叶的生活史故事,是一部从性别视角出发的社会史或曰历史人类学著作。其不仅挖掘并重现了以往被忽略或遮蔽的故事和历史,更打开或呈现了有别于中国现代性主流叙事、依据普通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逻辑所构建的集体化记忆。
■ 吴小英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新史学理念的传播,包罗万象的新的研究和书写模式不断涌现,以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记忆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兴盛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女性主义口述史更强调女性作为边缘群体在塑造历史和自我的过程中被忽略的经验,因而倡导不仅要让女性重新“浮出地表”,更重要的是借助底层的发声打开一种重新界定历史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历史学家贺萧的新书《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算不上典型的历史著作,更像是性别视角的社会史或者历史人类学著作。
贺萧与她的中方合作者高小贤一起历经十载(1996年~2006年),在陕西农村进行了田野调查,搜集了当地72位60~80多岁老年妇女关于20世纪中叶的生活史故事。其学术意义不仅仅在于挖掘并重现以往被忽略或遮蔽的故事和历史,更在于打开或呈现了有别于中国现代性主流叙事、依据普通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逻辑所构建的集体化记忆。
革命的日常生活样貌及其呈现
革命不单单是墙上的标语,也不仅仅是文件中的宣传条目,甚至不单纯是历史教科书上写就的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运动的总结。它渗透于普通人的境遇和选择中,因而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多面性。《记忆的性别》一书就是希望呈现革命的这一面向。
作者选取了“集体化”作为这种呈现的核心议题和年代,并将农村妇女这一称之为“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作为考察的中心和发声的主体。在她看来,妇女既是革命性变革的对象,也是这种变革行为的能动者。自1949年以来历次的集体化运动或政策实践中,每一段历史或事件都会带来农村社会的重组和剧变,而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被吸纳、被动员、直至积极参与其中并对国家运动做出回应,这一过程本身构成了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作者在访谈中也发现,关于集体化的记忆存在着“令人惊奇的性别差异”。相比之下,男人们比妇女们“更严密地遵循着官方用语和历史分期”,并极少谈论他们的私人生活。因而询问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一系列变革,包括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和婚姻等这些带有明显社会性别指向的领域,恰恰能够展现主流叙述中那些被忽略的革命样貌的蛛丝马迹。
有趣的是,贺萧发现访谈中男人通常会按照国家话语提供的“教科书般规范的”正式事件或运动顺序来讲述他们的记忆,比如“解放前”和“解放后”、土改、互助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等等。而除妇女干部之外,一般妇女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却颇为不同,她们会对这些顺序和内容进行“挪用和修改”,然后以更加私人的方式“命名”一种不同于“正史”和男人记忆的时间,例如结婚出嫁的时间、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等等。
出于对这些相互交叠的多重时间的尊重,该书除开篇之外,巧妙地用被访妇女一生中经历的不同身份角色作为全书其他各章的标题,并以它们为线索将不同时代串联起来。这些标题和身份包括寡妇、领导干部、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模范、劳动者、叙述者等,乍一看有点杂乱无序,但却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一般,分别展示了漫长的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在面对国家、集体、传统、家庭等不同情境时所做出的调试和应对,以及其间纠缠于个人的“家庭时间”与国家的“运动时间”之间的故事和感受,给读者呈现了一种与“大历史”中描述的革命不一样的观感。
介于家与国之间的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尤其是集体化历史无法绕过的问题。然而学界对这一问题是有争议的,社会主义初期的妇女解放或被视为一种“未完成的”或者“被延迟了的”革命,或被斥为自上而下国家恩赐的、因而妇女自身“失语”的打了折扣的解放。贺萧的研究似乎并无意卷入这些争论,但书中却以这些跨时代亲历者不无琐碎的讲述侧面回应了这一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将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放在了农村妇女介于家与国之间的具体生活实践中。
在这里,“‘国家’不再是一个外部的、无关紧要的存在,而是常常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如妇女领导、积极分子或劳动模范”;“解放”也不仅仅是诉苦或送童养媳回家,而是结束饱受饥饿和危险的“栖惶”(用来描述苦难的陕西方言)状态、走向稳定有序的日子的“分界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妇女被告知第一次有了走出家门到外面去的机会,妇女解放被叙述为“是一场进入此前被禁止的社会空间的运动”,与那种妇女被迫“幽居在家”、与世隔绝的“封建秩序”形成鲜明对照。
因而“解放”对于这些农村妇女来说从来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行动指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解放却把妇女抛在了家与国之间双重选择的张力中。书中被访妇女曹竹香的故事就很典型,她虽历经苦难和奋斗成了出色的地方劳模和干部,但在个人生活上却一直拒绝再嫁,恪守着主流宣传中被视为“封建残余”的寡妇贞节传统。贺萧认为,正是这种代表传统“妇德”典范的形象,使她在当地更有威望和影响力。贺萧还发现,访谈中一再出现的那种母亲夜间在灯下弯腰低头做针线活的叙事,并不像影视作品中那么充满浪漫煽情,而是代表了农村妇女对过去整整一个时代她们付出的看不见的劳作和艰辛不堪回首的记忆。而所有这些关于美德和辛劳的讲述,在今天这个她们称之为“翻身翻得太厉害了”的时代都已遭到怀疑或漠视,因而也成为这些失落的老年叙述者表达对当下处境的不满以及抵御被现代性抛弃的命运的自我安慰剂和力量。
性别化记忆与被“污染”的历史
《记忆的性别》一书在方法论上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口述史方法能否用来还原真实的历史以及如何处理可能有遗漏或变形的口述史料,在史学界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贺萧从一开始就不把本书的目标定义为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她只是希望在以往以简化的“运动时间”为框架的历史记录之外,寻找社会主义在远离国家宣传中心的农村地区以及女性参与者那里如何被理解和记忆的方式。由此,问题便从“发生了什么”转向“还记得什么”以及“讲述了什么”。
然而跟记忆密切关联的还有叙述方式本身的局限。贺萧发现,访谈中不乏“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的标准套路,也不乏把回忆中的20世纪50年代故事与当下的个人生活处境或忧思搅和在一起的陈述。这些杂乱无序的叙事结构,有时甚至充满了错误、遗漏、挪移或张冠李戴。贺萧的做法是一方面通过不同视角的材料(比如文字记载和对男人的口述材料等)之间的对照和检验来重新拼接和解读被访妇女的叙述,另一方面恰好从被访者的忽略、隐藏、加工或者有选择的记忆和表述中探究其背后的行为意义。
也就是说,作者退居到甚至不追求记忆和讲述本身的真实与否,因为她坦然接受所有的口述资料实际上都受到了讲述者本身的“污染”,“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因而本书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探究这些农村妇女为什么会如此讲述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以及这些貌似脱离常规的女性叙事方式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这一关于“记忆是如何性别化的”探究,恰恰揭示了这些农村妇女精心塑造的自我记忆中进步与伤痛交错并行的叙事背后所指向的那些未被言说的不平等状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